
-
中医自我发展的哲学研究初探
中医自我发展的哲学研究初探
【摘要】 中医与西医各有自身的思想轨道,所以在各自“自我”的视角上指责对方不可取;双方在哲学基础、身体观和方法论上自成体系,以现代西医理论解释中医只会使中医丧失了自我解释的能力。中西医两者沟通的渠道是实践的效果而非理论的解释。唯有保持自己的理论解释系统,中医的发展才有可能。
【关键词】 中医 西医 哲学基础 身体观 方法论 中医解释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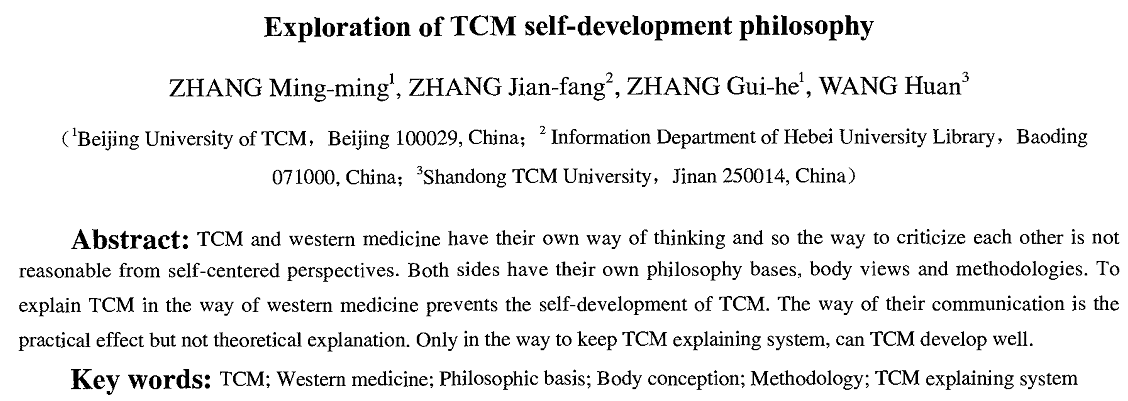
近百年来,中医的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中医存废之争”到“中医科学化之争”,从“废医存药”到方舟子的“废医验药”,乃至张功耀教授的《告别中医中药》,论争百年,余响不绝,是非优劣一言难尽。在中西医的互动中,我们更应看到二者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都应该成为承载人类健康舟车并行不悖之两轮。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更需要中医站稳脚跟,保持自己的主体地位,主动适应,而不是被动让步。中医西医,互为自我和他者自从有了中西医的区分,双方就有了彼此外在于主体,同时又给予主体定位的象征物。就中医看来,中医是自我,西医是他者;反之亦然。二者的论争模式在实质上就是拉康的“四角游戏”。一主体向另一主体即“他者”言说,由于在象征的层面上存在着一种被称为“语言之墙”的障碍物,所以前者无法直接告诉后者。主体的言说无法到达“他者”,却只能回到自我¨1]。中医这一主体的言说实际上无法真正到达另一个主体即“他者”,也就是西医。不存在一种所谓的主体间性,要说有一种相互的交流活动,那也只能是想象的主体间言语活动,即一主体自我(中医)与另一主体自我(西医)在想象层面上的言语交流活动。也就是中医在与想象中的西医对话,最后的言语活动表现为,主体(中医)向他人的像即他人自我言说,借助于他人自我与主体自我之问的想象关系,主体的言说又回到了自我(中医),西医对于中医指手画脚也未尝不如此。鉴于中西医自恋性的立场,这一想象的主体问关系不可避免地表现为一种你死我活的争斗。自我自恋认同他人,就是想把他人作为对象捕捉其中,就是企图取而代之;同样,他人自我也无时无刻不在期待着取代作为其他人的自我。中医以中医眼中的西医与西医以西医眼中的中医进行交锋,彼此不能说服,深究下去,就是中西医到底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同行的问题。就中医而言,究其本身是如何探究自己的研究方法,保持自身理论解释体系的问题。中西医百年论争见证了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所以中西医之间的论争是一种想象的主体问关系,误认性的想象功能造就了各自以自我为代表的想象秩序,自我成为了异化的主体。现实的中医即使存在,也不是作为自己而是作为科学来存在的,本己的本在完全消解于科学。中医西医,同医不同一中医与西医都是研究人体科学,但是各自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
1.哲学基础不同中医学始终强调在动态变化中认识人体的生、长、壮、老、已,从而把握或预测疾病的演变趋势,确立相应的治则治法;又借助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运用类比、演绎、外揣等具体的思维方法,阐述一系列医学问题。既重视各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以及内在联系,也强调人与自然界的协调统一,时空观上也是天人相应的,运用五行,干支和独特的中国天文学来支撑起中医理论的整个框架。秉承中国文化的精神,方法论上中医取中和之道,参阴阳、五行、三焦来辨证,和于中而施治。西医受西方哲学的特点影响,力主探求构成本原,注重结构分析,世界是“构成”的,而非“生成”的。医学研究愈益向微细方向深入,基因研究是为代表。尽管西方兴起的后现代哲学明确提出弃置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转而表达出关注生命意义的转向,甚至医学界出现了“时间医学”的探讨,毕竟与天人合一的中国时空观有质的不同。现实中最为可悲的是,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歪曲了对中医的哲学研究,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对中医学进行西式的疏解。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中医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的文化母体中寻求,未来的发展方向上中医哲学的发展将取决于它在当代的进展。中医哲学在当代的进展又取决于它的母体——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因此以中国文化为本,是涵养中医长存的根。
2.身体观不同中医的身体观倡导身心合一,身体是生命意义的原点。身体不再是客体,也不再是具体的身体,而是锁定在主体自身的感受方式。古代相当一部分学者主张以气为本体,当代在对研究方法的理解上,有学者主张以身体为本体。中医是身体之间的互动,医者进入到治疗现场,以身体构建治疗的图式,循身体运行的模式而非意识运行的模式,以自身作为研究的工具,用自己的身体倾听,让患者的身体说话。其戛不在于思维的意识,而在于行为的身体。在这个意义上,“身体”上升到一种本体的地位。此时“身”是作为一种植根于身的思维方式;“体”是体察,体会,是一种直接性,是用心进入到对象之内的理解,而非单纯的客观认识,是主客交融之下达成的理解;“观”是在天人合一的时空观和现场的互动关系中觉察整个情境,同时也反观自身,随时做出调整和改变,这也正是中医身体观的寓意所在。近代西医学实质上是身心二元分离的,注重用分析、化验的方法把握人的健康和疾病,具有浓厚的实证科学的色彩,尽管有了现象学的转向,例如以梅洛庞帝为代表的身心模糊的身体观,但是毕竟是不同于中医的医学文化。
3.研究方法不同以西方的方法学理论来衡量,勉强在总体的倾向上看,中医采取的是质的研究方法,西医偏向量的研究方法。二者的研究方法都是在主体_方法一客体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并且主体和客体都是相同的,唯有方法是截然区分的。由于文化的差异,西医是主体和客体区分开,以主体来审视客体,中医的主体和客体是合一的。西医的研究方法以量的研究为主,计数和定量的方法在近代西医学中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数理流行病学、药物分析、数理诊断等一批数理医药学的崛起,使得西医基础和临床医学在一定程度上走上了客观化、精确化的道路,西医学已经成为一门计量的医学。近年来又有西方学者呼唤定性的研究方法,如在临床护理上采用植根理论来从参与者的视角关注临床上的问题,力主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更好结合。中医的研究方法也不排斥数,但是中医的数并非单纯的定量,在定量的同时更规定了数的质性,所以是量与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用图象而非几何的特殊的数学方法,即“以数取象”的象数方法。在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中,也经常应用数,但这时的数大多已不具有量的含义,而是象的符号。如关于阴阳的“阴道奇,阳道偶”,关于五行的生成数等只有分类、区别、命名等定性的作用。中医对于“象”的认识,如面象、舌象、脉象等,更多的是从其色、形、态等方面进行定性认识,定量的把握较少。建构古中医理论最根本的依据正如李时珍指出的:“然内景隧道,惟反观者能照察之,其言必不谬也”]。中医的五行藏象系统与六经藏象系统都是定f生研究得出来的。在西方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彼此论战的同时,国内出现了以实验方法为纲,系统地阐述与中医有关的实验研究的理论。例如经过数理统计方法杂交的传统中医的诊断包括中医诊法实验研究方法、中医辨证实验研究方法、中医诊断动物实验方法和中医病证量化诊断及综合性研究等,在学界经常以起点高自居。大多的医学院教材对于质的研究方法没有丝毫的提及,却又丢掉了象数的实质,对于五行的真实来源都搞不清楚了。西方的研究方法取了一半,自己的象数理论几乎不懂,岂不是东施效颦,葬送中医指日可待。对于研究方法上定量与定性关系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可否认的是定量的起初已经有了一个潜在的定性,例如脾肾两助丸抗抑郁的实验研究概要,尽管这是一个量的研究,但是对于实验中的小白鼠已经有了一个质的规定一抑郁。抑郁是否是有根据的,是否来自于整个实验的情境,或者说实验的封闭情境究竟与开放的现实到底相差多远,这些都决定于学者的个人界定或者是群体接受程度。当然,定性不能也不能排斥定量的数据,最新的行动研究主张把数据作为自己的参考资料。定量的潜在危险在于一个有了一个莫须有的定性,否则接下来的数据都是空中楼阁。不顾事实与数量的定性,只能是一家之言。西方学者也在不断的警示,当研究者在他所从事的研究中忘却自己的主观性,自以为掌握了客观真理并进入了本真世界,但事实上这不过是“遗忘存在”的一种变形。不要轻易放弃中医的研究方法,更不要轻易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改良嫁接,保持自己纯粹的研究方法是正统中医的必然。保持了自己正统的研究方法,中医自然能够经得起西方研究方法的验证。
近一百多年来的“以现代医学解释中医”的闹剧使中医丧失了“以中医解释中医”的能力,中医学术理论沦为被现代医学任意解释的对象,中医渐渐成了“西方的中医”,中医学术理论成了西方文化视野下的中医学术理论。中医异化的国内国际背景,导致中医在回应现代医学挑战的过程中,自己先乱了自己的解释系统,中医和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文化知识变得整体性地失语l 5]。这种失语使得中医学术的言述方法、思维方式和制度方式丧失了科学性而走向异化。时至今日,认为“中医只有把《黄帝内经》中朴素直观的五行、阴阳、三焦、虚实、表里等辨证施治经验,用科学语言表达出来才能够为人所接受”这种观点的人仍旧很多。实际上学者只有探讨古天文学与医学之间关系的研究,才能够真正明白“阴阳五行”的本质不是对客观物质世界“朴素直观”的认知,而是对客观物质世界本质屙f生的象数思维认知。才能够真正明确中医西医,同医不同一,才能依据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科学知识和语言,用我们真正的母语,透析中医学术理论的脏腑、经络、气血等学说与阴阳五行八卦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才能真正恢复中医固有的解释系统,建立健全真正科学的中医学术理论体系。
中医,到底以怎样的姿态与西医同行同一个世界,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到底怎样同行?笔者认为首先应该走出自我中心,做到“去中心化”,不自以为是,不是去彼此防御,而是互相开放,可以质疑,但不是轻易否定,侉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争斗,和而不同;以一种更整合的视角看待身体这一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既结合现象学的要素,同时也具备实用的特征。不同的研究阶段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初期发现的阶段依据现象学的原则,面对现场本身,从参与者的视角上看问题,融入变化的过程中,依靠不断比较的方法和经验的整合作用;在理论成形的阶段,反观自己视角的同时,依据实证式的理解,产生自成体系的理论;评估的阶段,根据实用的标准并不断修正。这些阶段并非断开而是处于一个过程中。最终的理论是通过与现场的适合性,是否起作用,自我修正的能力,严密性,整合性等标准来判断的。要提—下这种研究方式的局限性,亦即以人为研究工具的不确定性,需要时间和历练,需要理论和实践上的敏感性,既要有通化材料的能力,又要有保持距离形成诊断的能力。另外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相同的可重复的操作能力,这不是产生理论的能力,而是自身的理论能否切合情境的能力,也即把握天人关系,为人所用。由此可见,当前中医与西医在实践的效果上彼此沟通是最为现实的,正如陈竺部长所言:中医有望对医学模式带来深远的影响。


.jpg)




